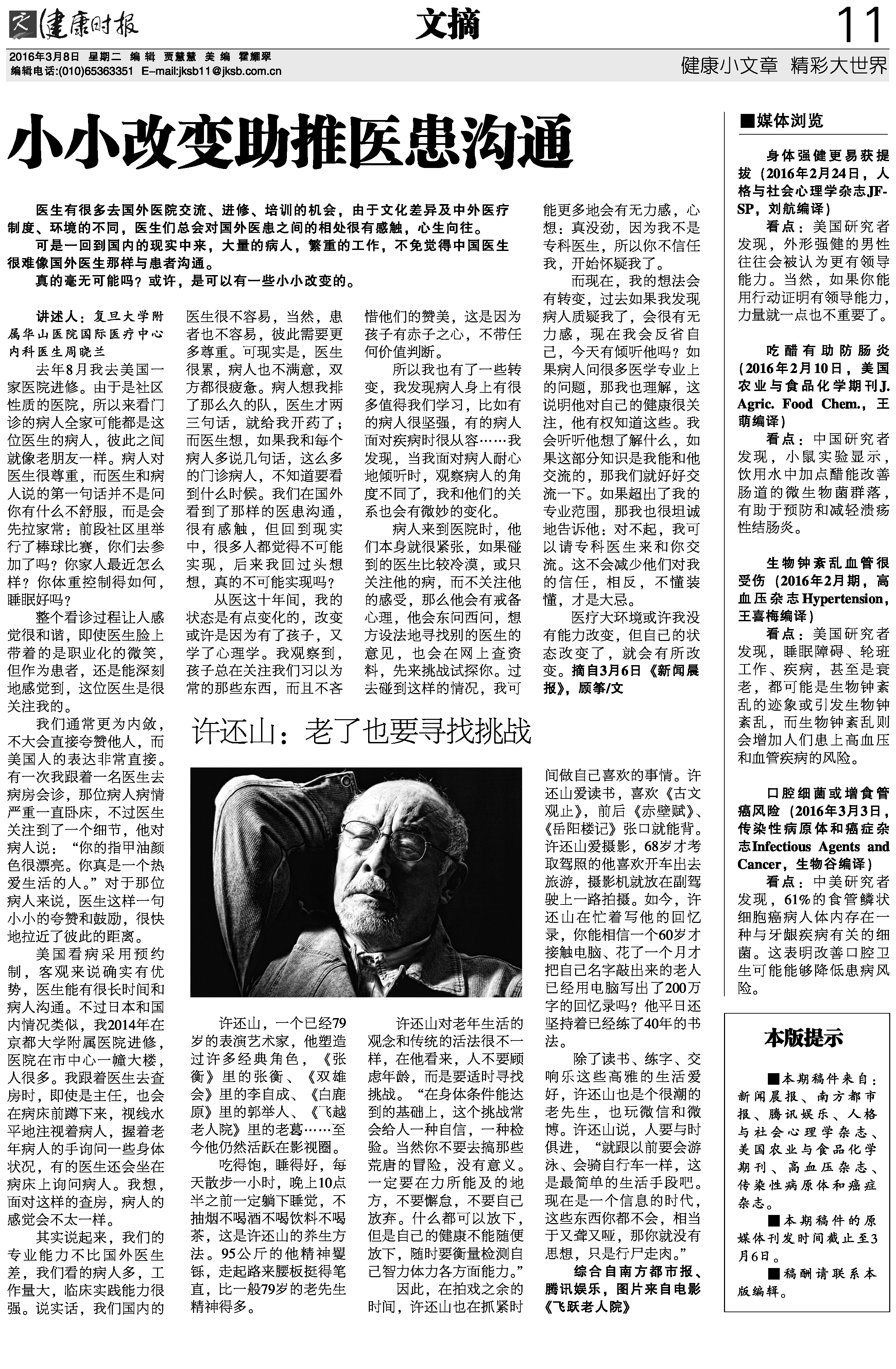可是一回到国内的现实中来,大量的病人,繁重的工作,不免觉得中国医生很难像国外医生那样与患者沟通。
真的毫无可能吗?或许,是可以有一些小小改变的。
讲述人: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内科医生周晓兰
去年8月我去美国一家医院进修。由于是社区性质的医院,所以来看门诊的病人全家可能都是这位医生的病人,彼此之间就像老朋友一样。病人对医生很尊重,而医生和病人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问你有什么不舒服,而是会先拉家常:前段社区里举行了棒球比赛,你们去参加了吗?你家人最近怎么样?你体重控制得如何,睡眠好吗?
整个看诊过程让人感觉很和谐,即使医生脸上带着的是职业化的微笑,但作为患者,还是能深刻地感觉到,这位医生是很关注我的。
我们通常更为内敛,不大会直接夸赞他人,而美国人的表达非常直接。有一次我跟着一名医生去病房会诊,那位病人病情严重一直卧床,不过医生关注到了一个细节,他对病人说:“你的指甲油颜色很漂亮。你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”对于那位病人来说,医生这样一句小小的夸赞和鼓励,很快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美国看病采用预约制,客观来说确实有优势,医生能有很长时间和病人沟通。不过日本和国内情况类似,我2014年在京都大学附属医院进修,医院在市中心一幢大楼,人很多。我跟着医生去查房时,即使是主任,也会在病床前蹲下来,视线水平地注视着病人,握着老年病人的手询问一些身体状况,有的医生还会坐在病床上询问病人。我想,面对这样的查房,病人的感觉会不太一样。
其实说起来,我们的专业能力不比国外医生差,我们看的病人多,工作量大,临床实践能力很强。说实话,我们国内的医生很不容易,当然,患者也不容易,彼此需要更多尊重。可现实是,医生很累,病人也不满意,双方都很疲惫。病人想我排了那么久的队,医生才两三句话,就给我开药了;而医生想,如果我和每个病人多说几句话,这么多的门诊病人,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。我们在国外看到了那样的医患沟通,很有感触,但回到现实中,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实现,后来我回过头想想,真的不可能实现吗?
从医这十年间,我的状态是有点变化的,改变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,又学了心理学。我观察到,孩子总在关注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,而且不吝惜他们的赞美,这是因为孩子有赤子之心,不带任何价值判断。
所以我也有了一些转变,我发现病人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,比如有的病人很坚强,有的病人面对疾病时很从容……我发现,当我面对病人耐心地倾听时,观察病人的角度不同了,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会有微妙的变化。
病人来到医院时,他们本身就很紧张,如果碰到的医生比较冷漠,或只关注他的病,而不关注他的感受,那么他会有戒备心理,他会东问西问,想方设法地寻找别的医生的意见,也会在网上查资料,先来挑战试探你。过去碰到这样的情况,我可能更多地会有无力感,心想:真没劲,因为我不是专科医生,所以你不信任我,开始怀疑我了。
而现在,我的想法会有转变,过去如果我发现病人质疑我了,会很有无力感,现在我会反省自己,今天有倾听他吗?如果病人问很多医学专业上的问题,那我也理解,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很关注,他有权知道这些。我会听听他想了解什么,如果这部分知识是我能和他交流的,那我们就好好交流一下。如果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,那我也很坦诚地告诉他:对不起,我可以请专科医生来和你交流。这不会减少他们对我的信任,相反,不懂装懂,才是大忌。
医疗大环境或许我没有能力改变,但自己的状态改变了,就会有所改变。摘自3月6日《新闻晨报》,顾筝/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