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辉:我的故事
谈工作:
关键失误让我更加专注
有些人夸我:“从来没见过你出错,厉害!”我急急否认,在我熟识的同行中,未有一人做到永远精准无误,至于我,更不是“播神”。
我迄今出过的最大的失误,是在2008年5月13日凌晨的直播中,当播到一组外国领导人向我国发来的慰问电时,我不知怎么回事,竟将“慰问电”说成了“贺电”!
两个字脱口而出的一瞬间,我眼前如一道霹雳闪现,紧跟着冷汗涔涔而下,困倦一扫而光。我急忙纠正过来,强自镇定地继续将后面的内容播完。
直播结束,同事们都忙着做播后的整理工作,没有人和我提起这个失误,也许大家都地不想给我更多压力吧。我沮丧地回到办公室,暗骂自己:“这样低级的失误在这个时候出现,简直是对灾区人民犯罪啊!”
我做好了迎接网上无数板砖的准备。但意外的是,网络上有关我这个失误的留言绝大多数都是表示理解的,很多网友说“谁没有口误的时候啊,主持人凌晨直播,太疲倦了,能理解”“工作很辛苦,千万别因此受处分啊”等。观众的宽容令我很感动,也愈发令我惭愧。
我一遍遍反复检讨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,熬夜时状态疲劳?困倦?直播时信息纷乱?庞杂?这些都可以是理由,但都不应该是理由,如果接受这样的理由,那就是对自己的纵容、对职业的不尊重。
归根结底,问题还是出在不够专注,而这正是直播的大忌。我很感谢观众的宽容,也很感谢领导和同事们的体谅,是他们帮我一点点减轻了心理上的负担,让我能继续有机会用更认真的工作来弥补过失。
但我提醒自己,无论如何,不能滥用这些宽容和体谅,否则就辜负了这些宽容和体谅。
对于直播中的失误,我最出名的一次大概是“鼻涕门”。
那是2010年4月2日,中午直播的《新闻30分》。一条急稿送进来,我还没来得及完整看一遍,镜头已经切到了我面前的摄像机。因为紧急,我要低头看稿播出,一些地方要抬头看摄像机。
播了没几句,我这有过敏性鼻炎的鼻子,鼻涕开始服从地球引力的作用了。
不专注是直播的大忌,可这时候我已不可能不生出杂念,一边震慑心神别出错,一边脑子里飞速判断、决定到底该怎么办。 擦一下?可能保证一下就完全解决问题吗?如果不行,恐怕结果更糟。不擦?万一真的流过界岂不是更不严肃了?这是重要的时政新闻啊!
两害相权取其轻,我决定不抬手擦,尽量多抬头播,必须低头时就借着镜头的角度偷偷吸一吸鼻子,同时不能过于慌张地加快语速,不能让脸上有任何不该有的表情。就这样坚持播完,没出现最坏的情况,可鼻涕到底挂在了鼻子下面,而且吸鼻子的声音也能听得出来。
网络上的反应可谓见仁见智。有人说:“康辉流着鼻涕可没有出现任何差错,感动于他的敬业精神。”也有人说:“流着鼻涕播新闻太不严肃了。”还有人说:“这种意外不属于央视处罚范畴吧?”更有人建议央视应当制订应急预案等。
从我经历过的一些事包括“鼻涕门”,我看到了很多善意、包容、理解和理性的关注。不过,我不敢接受任何关于敬业的褒奖,不在于它引起了网络围观,而在于我痛感自己并不够敬业。
做这个职业,身体是本钱,调整不好自己的身体,就等同于不敬业。我在当时做出了所有可能的反应中最适当的一种,但依然改变不了失误本身给新闻播出带来的影响。这记重锤,砸得好痛,也砸得好正。
谈亲情:
母亲去世后,我才遗憾没能好好陪她
2018年11月15号早上8点,我在机场接到了姐姐的电话:妈妈走了。
出差的前两天,我回去看望妈妈,要赶回北京的时候,我在她耳边说:“妈,一定等我回来。”可是,妈妈没有等我,她大概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吧。
人到中年,像这样的离别本不属意外,但无论做了怎样的心理准备,那一刻,仍然有着太多的痛,太多的不舍与遗憾。妈妈一生都好强,最后在病榻上缠绵的那两个月,该算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无助和脆弱的时候。
而我最后陪伴她的时间,就像过去这些年里一样,少得可怜。在电话里听到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忙你的吧。”这几个字里,究竟包含着多少意思?
上次回家,我在整理一些妈妈住院用的东西时,忽然发现,一向都是整齐细致、会将物品分门别类归置得很好的妈妈,有很多东西竟也凌乱起来了。我蓦然心惊,她更多时间独处空屋的时候,大概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心气儿去做这些事了。而这些,竟都是我疏忽已久的。
这些年,我竟再也没有与妈妈合影。尽管拿起手机拍张照片是如此容易,可我翻遍了先后更换的几个手机,竟一张也没有。我是多么坚信日子还将长长久久?还是压根就忽视了她的存在?
同样,我竟没有留下一件妈妈亲手为我织的毛衣,反而匆匆追逐着那些所谓新鲜的时尚。如今,抚着她最后给自己织的还没有来得及穿的毛衣,那种熟悉的仿佛妈妈怀抱一样的感觉倏忽包围了我,那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妈妈的气息。
我想回家,把用了几十年的那张竹躺椅带回来,那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,妈妈到四川出差,辗转了几个省份一路背回来的。耳边好像又听到了妈妈常抱怨我的那句话:“那么大个人,这点东西都嫌沉。”
我想回家,把妈妈的那几盆花再浇浇水。她似乎从来不喜欢养小动物,但对植物情有独钟。几盆芦荟、富贵竹是她晚年撑着病体极力悉心呵护的植物。如今,都枯萎了。
我很想再吃几块妈妈做的酱牛肉,也许别人会觉得香油的味道未免重了些,可只有那样的味道才是我心底固执地认为酱牛肉该有的味道。
我很想再陪她好好说一会儿话,这些年能静静地坐下来陪妈妈聊聊天的时间,少之又少。再加上我遗传了她的急脾气,在亲人面前,放松的同时也多了放肆。常常两句话没过,会忍不住和妈妈戗起来。很多时候,我就只做一个听众,听她重复那些话,也难免一耳进一耳出。可如今,我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再听她唠叨几句,听不到了。
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所谓前世今生,但这一刻我坚定地相信,妈妈没有离开,她的灵魂永在,她会永远记得她的孩子们,她会时时抚摸着我们的灵魂,就如同小时候时时抚摸着我们的身体一样。
妈妈的告别仪式举行时,我仍在万里之外。按着姐姐告诉我的时刻,我朝向故乡的方向,给妈妈长长地磕了三个头。
摘自《康辉:平均分》,康辉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供图
谈工作:
关键失误让我更加专注
有些人夸我:“从来没见过你出错,厉害!”我急急否认,在我熟识的同行中,未有一人做到永远精准无误,至于我,更不是“播神”。
我迄今出过的最大的失误,是在2008年5月13日凌晨的直播中,当播到一组外国领导人向我国发来的慰问电时,我不知怎么回事,竟将“慰问电”说成了“贺电”!
两个字脱口而出的一瞬间,我眼前如一道霹雳闪现,紧跟着冷汗涔涔而下,困倦一扫而光。我急忙纠正过来,强自镇定地继续将后面的内容播完。
直播结束,同事们都忙着做播后的整理工作,没有人和我提起这个失误,也许大家都地不想给我更多压力吧。我沮丧地回到办公室,暗骂自己:“这样低级的失误在这个时候出现,简直是对灾区人民犯罪啊!”
我做好了迎接网上无数板砖的准备。但意外的是,网络上有关我这个失误的留言绝大多数都是表示理解的,很多网友说“谁没有口误的时候啊,主持人凌晨直播,太疲倦了,能理解”“工作很辛苦,千万别因此受处分啊”等。观众的宽容令我很感动,也愈发令我惭愧。
我一遍遍反复检讨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,熬夜时状态疲劳?困倦?直播时信息纷乱?庞杂?这些都可以是理由,但都不应该是理由,如果接受这样的理由,那就是对自己的纵容、对职业的不尊重。
归根结底,问题还是出在不够专注,而这正是直播的大忌。我很感谢观众的宽容,也很感谢领导和同事们的体谅,是他们帮我一点点减轻了心理上的负担,让我能继续有机会用更认真的工作来弥补过失。
但我提醒自己,无论如何,不能滥用这些宽容和体谅,否则就辜负了这些宽容和体谅。
对于直播中的失误,我最出名的一次大概是“鼻涕门”。
那是2010年4月2日,中午直播的《新闻30分》。一条急稿送进来,我还没来得及完整看一遍,镜头已经切到了我面前的摄像机。因为紧急,我要低头看稿播出,一些地方要抬头看摄像机。
播了没几句,我这有过敏性鼻炎的鼻子,鼻涕开始服从地球引力的作用了。
不专注是直播的大忌,可这时候我已不可能不生出杂念,一边震慑心神别出错,一边脑子里飞速判断、决定到底该怎么办。 擦一下?可能保证一下就完全解决问题吗?如果不行,恐怕结果更糟。不擦?万一真的流过界岂不是更不严肃了?这是重要的时政新闻啊!
两害相权取其轻,我决定不抬手擦,尽量多抬头播,必须低头时就借着镜头的角度偷偷吸一吸鼻子,同时不能过于慌张地加快语速,不能让脸上有任何不该有的表情。就这样坚持播完,没出现最坏的情况,可鼻涕到底挂在了鼻子下面,而且吸鼻子的声音也能听得出来。
网络上的反应可谓见仁见智。有人说:“康辉流着鼻涕可没有出现任何差错,感动于他的敬业精神。”也有人说:“流着鼻涕播新闻太不严肃了。”还有人说:“这种意外不属于央视处罚范畴吧?”更有人建议央视应当制订应急预案等。
从我经历过的一些事包括“鼻涕门”,我看到了很多善意、包容、理解和理性的关注。不过,我不敢接受任何关于敬业的褒奖,不在于它引起了网络围观,而在于我痛感自己并不够敬业。
做这个职业,身体是本钱,调整不好自己的身体,就等同于不敬业。我在当时做出了所有可能的反应中最适当的一种,但依然改变不了失误本身给新闻播出带来的影响。这记重锤,砸得好痛,也砸得好正。
谈亲情:
母亲去世后,我才遗憾没能好好陪她
2018年11月15号早上8点,我在机场接到了姐姐的电话:妈妈走了。
出差的前两天,我回去看望妈妈,要赶回北京的时候,我在她耳边说:“妈,一定等我回来。”可是,妈妈没有等我,她大概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吧。
人到中年,像这样的离别本不属意外,但无论做了怎样的心理准备,那一刻,仍然有着太多的痛,太多的不舍与遗憾。妈妈一生都好强,最后在病榻上缠绵的那两个月,该算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无助和脆弱的时候。
而我最后陪伴她的时间,就像过去这些年里一样,少得可怜。在电话里听到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忙你的吧。”这几个字里,究竟包含着多少意思?
上次回家,我在整理一些妈妈住院用的东西时,忽然发现,一向都是整齐细致、会将物品分门别类归置得很好的妈妈,有很多东西竟也凌乱起来了。我蓦然心惊,她更多时间独处空屋的时候,大概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心气儿去做这些事了。而这些,竟都是我疏忽已久的。
这些年,我竟再也没有与妈妈合影。尽管拿起手机拍张照片是如此容易,可我翻遍了先后更换的几个手机,竟一张也没有。我是多么坚信日子还将长长久久?还是压根就忽视了她的存在?
同样,我竟没有留下一件妈妈亲手为我织的毛衣,反而匆匆追逐着那些所谓新鲜的时尚。如今,抚着她最后给自己织的还没有来得及穿的毛衣,那种熟悉的仿佛妈妈怀抱一样的感觉倏忽包围了我,那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妈妈的气息。
我想回家,把用了几十年的那张竹躺椅带回来,那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,妈妈到四川出差,辗转了几个省份一路背回来的。耳边好像又听到了妈妈常抱怨我的那句话:“那么大个人,这点东西都嫌沉。”
我想回家,把妈妈的那几盆花再浇浇水。她似乎从来不喜欢养小动物,但对植物情有独钟。几盆芦荟、富贵竹是她晚年撑着病体极力悉心呵护的植物。如今,都枯萎了。
我很想再吃几块妈妈做的酱牛肉,也许别人会觉得香油的味道未免重了些,可只有那样的味道才是我心底固执地认为酱牛肉该有的味道。
我很想再陪她好好说一会儿话,这些年能静静地坐下来陪妈妈聊聊天的时间,少之又少。再加上我遗传了她的急脾气,在亲人面前,放松的同时也多了放肆。常常两句话没过,会忍不住和妈妈戗起来。很多时候,我就只做一个听众,听她重复那些话,也难免一耳进一耳出。可如今,我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再听她唠叨几句,听不到了。
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所谓前世今生,但这一刻我坚定地相信,妈妈没有离开,她的灵魂永在,她会永远记得她的孩子们,她会时时抚摸着我们的灵魂,就如同小时候时时抚摸着我们的身体一样。
妈妈的告别仪式举行时,我仍在万里之外。按着姐姐告诉我的时刻,我朝向故乡的方向,给妈妈长长地磕了三个头。
摘自《康辉:平均分》,康辉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供图
(运营:吴芯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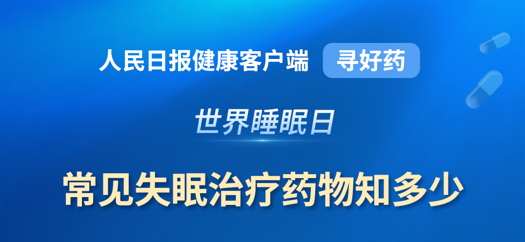








网友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