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母尚属中龄时
两代人生活互助
2001-2011的十年,父母尚属“中龄老人”,我则渐入低龄老人阶段。双方体力和精力良好,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,可ν上佳的合作状态。
父亲生于1930年,母亲比他年长一岁。我是长女,1951年生人;底下一个妹妹、一个弟弟,分别生于1954和1968年。
2001年,父母来北京,与弟弟生活在一起。平日里只要我在京,ÿ个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园,时不时一起去听京剧或看美展。那时父亲腿部的静脉曲张致使皮肤变色,ÿ隔十天半月,我都陪他去小庄医院见大夫。
2006年,弟媳带着女儿自西安来京与弟弟团聚。母亲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,不能适应家庭环境变化,数次哭求父亲搬离。我居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¥有λ熟人迁往他处,我赶紧筹资将那旧房买下,又安排父母住进了烟台一家老年公寓。
两月之后,他俩带着阳光海风留驻的健康肤色回京入住新家,与我开启了“一碗热汤”距离的生活互助模式。ÿ天中午和傍晚我都下¥与他们一同就餐,邻居都羡慕:“您到这把年纪还能吃上父母做的饭,多幸福啊!”
同年,母亲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症,父亲的腿疾也δ见好。住地附近的二三级医院皆在两公里之内,父母几乎ÿ周二都步行去见大夫。周末我陪父母先去公园健走,再到弟弟家聚餐。一时间,家人团聚其乐融融。
父母健康突发性下滑
开始失去平衡
父母在80岁左右的时候,身体功能就已显著下降。例如耳背,听不见电话铃和门铃;又如,父亲行走愈益吃力,母亲渐次失去瞬间记忆和一些扫地开锁之类的生活技能。为此他们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,只保留了逛公园、去医院和买菜做饭的活动。为了弥补他们弱化的功能,我选购了助听器、拐杖和手表式定λ仪,并安装了无线门铃。
2012年冬,北京雾霾加剧。这对肺部纤维化的母亲和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父亲,实属不利。自当年秋末,在父母老友介绍下,我们姊妹轮流陪伴他们在海口过冬,弟弟则在春节前往探望。
那一年,父母的幸福感明显提高。海口气候温润、空气优良、蔬果鲜嫩、海产ζ美,他们还能时不时与老友同事相互串门。到2014年春,父母还不愿回京。
2015年再赴海口,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突发性下滑。
第一,失去同龄社交对象。住在400米开外的同事因糖尿病足部腐烂,导致全身器官衰竭而亡。住在100米外的张阿姨去世,父亲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打电话报丧,不想对方竟已逝世一个多月。
第二,身体功能江河日下。父亲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,施用各种方子不见好转。父亲变得脆弱易怒。我和妹妹只能忍耐并相互约定,照料父母要尽力做到“防感ð、防感染、防跌倒”,对母亲尤其要“防走失”。
第三,智力愈益退化。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又添狂躁表现,时不时哭闹一场,总是缠着父亲要下¥(我请人更换了门锁,她无法自行外出)。尤其是午休和半夜,父亲常被折磨得睡眠不足。
妹妹陪父母乘班机回京,二老下不了舷梯,乘务员调用升降机和轮椅,才把他俩运出机场。这一旅程不仅使妹妹的精力体力几近崩溃,也坚定了我另寻照料途径的决心。
做出抉择
把父母送入养护中心
2016年3月伊始,我就连篇累牍地向父亲发送机构养老的资料和劝说信。他要ô不回答,要ô顾左右而言他。
3月15日,我们姊妹仨陪同父亲去望京医院见大夫,医生叮嘱,患者血液回流不畅,导致腿脚水肿和皮肤溃疡,要穿上弹力袜或像士兵那样打绑腿。父亲腿脚肿得厉害,弹力袜肯定穿不进去。
妹妹和我对望一眼,仅打绑腿一项,我俩就谁也干不了。此前我们姊妹仨就已分头考察京城的养老机构。从医院出来,妹妹和我立即开始新一轮走访。我提出的选择标准,一是有可靠的医疗条件,能提供基本的健康维护;二是入住者大多人文素质良好,有助老人交往;三是交通方便,有利于亲属探视;四是性价比较高,家庭财务能够承受。3月19日施工队将在我的宿舍¥更换厨卫水管,若不能将父母安排妥当,他们室内磕绊的风险无疑陡增。
根据经济所一λ前辈同事的建议,我和妹妹于3月16日驱车前往一家大型养护中心考察,我和妹妹都觉此地可心。3月18日,我们姊妹仨就把父母送入了养护中心。
母亲视养老院为η途,乍一听我们的建议就大哭:“我生了她(朱玲),为她做这做那,她却不要我了!”还是父亲一番劝说,才阻止了母亲继续把我推向道德泥坑。
入住养护中心那天,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场。我到家就给父亲发短信,请求他和母亲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,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。父亲也短信回复:“慢慢适应吧。我哭是你们要走了,心里一阵凄凉感”。
我曾想过带着父母一起住养老院。可是考虑到自己依然衷情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经济学研究,就放弃了这一设想。只要我们姊妹仨都在北京,可以做到隔天有人探望。
次日上午父亲发来微信:“这里服务相当好,昨天今天已换药两次,很专业。”大夫打的绑腿自然紧实,老父的伤口也不再淌水。他和母亲对这里的食宿和服务非常满意。
摘自2016年《经济学家茶座》杂志总第72辑
父母住进养老院之后
65岁女儿朱玲:
75岁我就考虑进养老院
2016年国庆节,父母入住养老院半年后,朱玲收到叔叔转发的她父亲的微信——“老伴失智是很折磨家人的,我已86岁,希望得一个猝死的病。”
她抓起电话就打,知道父亲熬不住了,迅速为母亲购买了“一对一”护理服务。电话那头,父亲为母亲的状态痛哭,既舍不得与母亲分开,又担忧费用因新的安排猛涨。
朱玲卖掉老家房子,结合父母此前存款,支撑几年再由她带着弟弟妹妹补差额。父亲最终同意。
在父母入住之后,朱玲郑重和好友商量了自己今后的养老计划——
第一,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,免得到高龄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;第二,好友结伴去,方便社交;第三,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,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服务;第四,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,因亲友多在北京;第五,现在就开始为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。
86岁父亲朱鸿程:
终于重新拥有自己的空间
年近九旬的朱鸿程从û想过晚年会在养老院过。更û想到的是,居然还过得不错。
护理员介入那晚,老伴起夜,由护理员照顾如厕,事后老伴睡得很好。而他虽听见但δ起身,所以也休息充分。因有护理员跟随,他不用担心老伴走丢、吃饭等问题。
他从女儿处看到不少长期照护的思考。“连续性长照,是比吃饭穿衣还优先的最基本生活服务。”
朱鸿程感同身受。他又有精力关注他喜欢的国家大事了。“我的精神世界还û有衰老,我不想当个糊涂人。”
重担卸下,才终于重新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。这是朱鸿程接受长期照护的意义。摘自2017年1月7日上海观察,王潇/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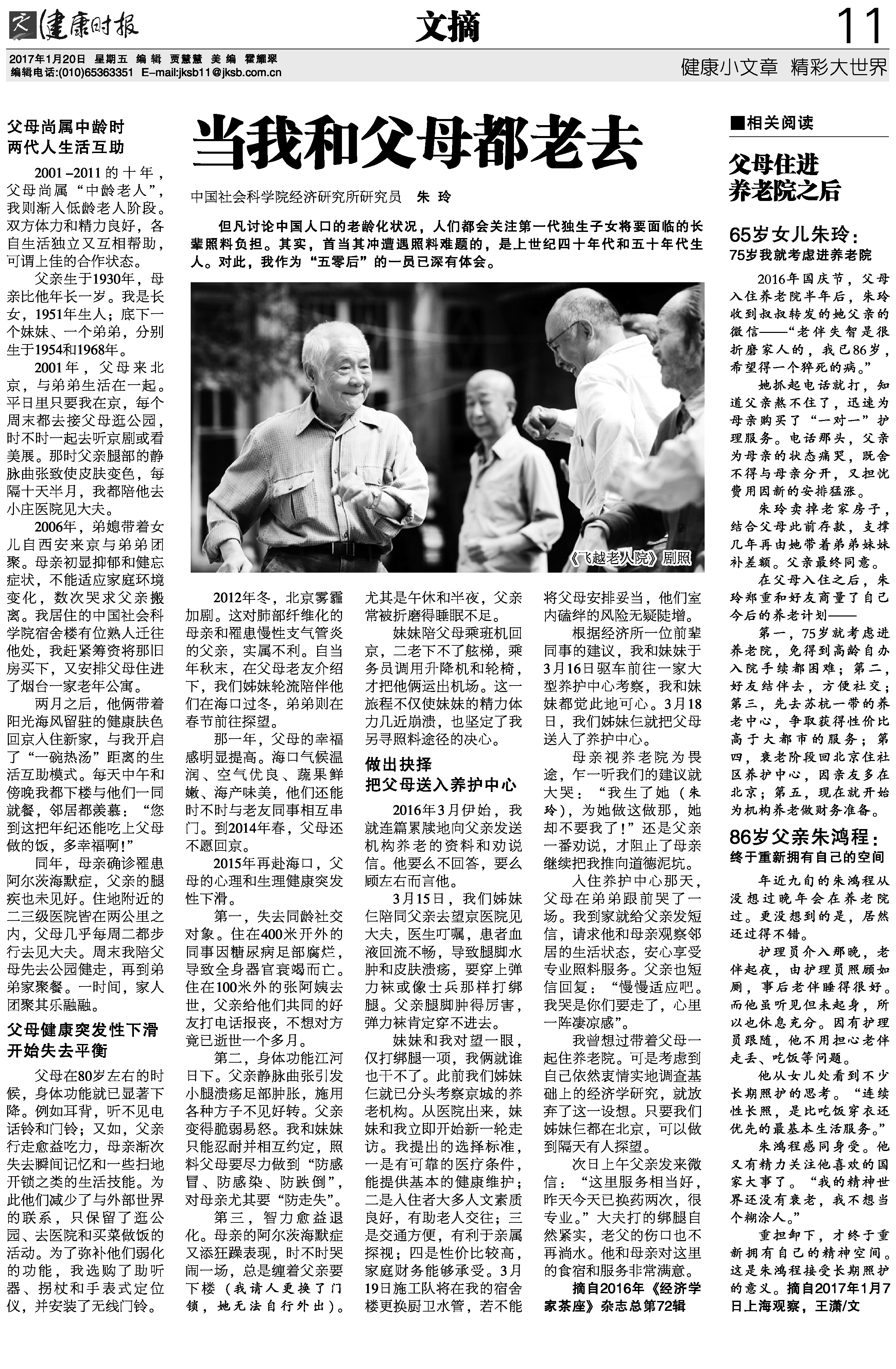

 下一篇
下一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