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清晨六点的马路,人很少,车子也很少,一切都还笼罩在轻薄的雾气里。我有点急迫地跑过两边还拉着铁闸门的小店,一口气跑过那几个红绿灯,穿过几条还未拥挤的横马路,跑进学校的那扇大门,穿过短短的才种上新树的林荫道,跑进那红彤彤的塑胶道。
那是个很平常的早晨,我一个人在操场里跑了20圈,手腕上的计步器“滴”地轻响了一声,我对自己说,“20,今天就到这里吧”。缓慢收住脚步,开始略微夸张地往前迈大步拉伸后腿的肌肉,并轮流甩动手臂。我突然意识到,不知不觉,已经这样跑了这么久,一个人。
这是我一个人跑步的第三年。
我喜爱的作家村上春树写过一本《当我谈跑步时,我谈些什么》的畅销书。我开始跑步的时候,这本书刚好在大陆出版,一时间许多人都在谈论这本书,很多人也都蜂拥而上说起自己喜欢跑步这件事。
可是事实上,身边每天与我一起跑步的同行者却非常少。而且跑步这件事,更像是孤独的运动,步伐和频率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节奏,很难凑到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苦行僧一般的节制生活,吸引了最初开始跑步的我。跑步的初衷不过是希望自己的身体累一些,晚上睡得好一些;之后变成了向喜爱的作家学习致敬的方式,我用每天跑满五公里的要求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,希望至少在跑步这一件事上向偶像看齐。
在度过最初的艰难的不适期之后,跑步这件事,很快变得非常纯粹。培养意志力和加强睡眠之类的动机完全不值一提,至于许多人跑步的初衷“要变得更瘦”对本来就很瘦的我来说,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。
摆动手臂,迈开步子,呼——吸——呼——吸,再多一圈,再跑一公里,说起来就是这么简单。
我后来一个人在很多地方跑过步。在冲绳的海边,有专门为跑者设计的塑胶跑道。法国有一个叫做Biarriz的小镇让人印象深刻。我每天早晨沿着酒店门前那一条石子路一直跑到海边,看一人高的白色浪花拍过来,再卷着泡沫退回去。韩国济州岛的跑道奢侈地绕岛一圈,凡是能看见海的地方,就有亮红色的标准两人道塑胶跑道。我绕过北京的紫禁城跑。最核心的皇宫,红墙围起的一整周,不折不扣跑下来,刚好是六公里。许多大学的操场都是很好的跑步地点。每一个出差过的城市,我都竭尽全力找一块安静的校园操场跑。
跑步让我随时随地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节奏,在陌生的城市,在阅读写作的时候,在任何时间,它都兀自在那儿咚咚跳动着,这节奏如此坚定,不容忽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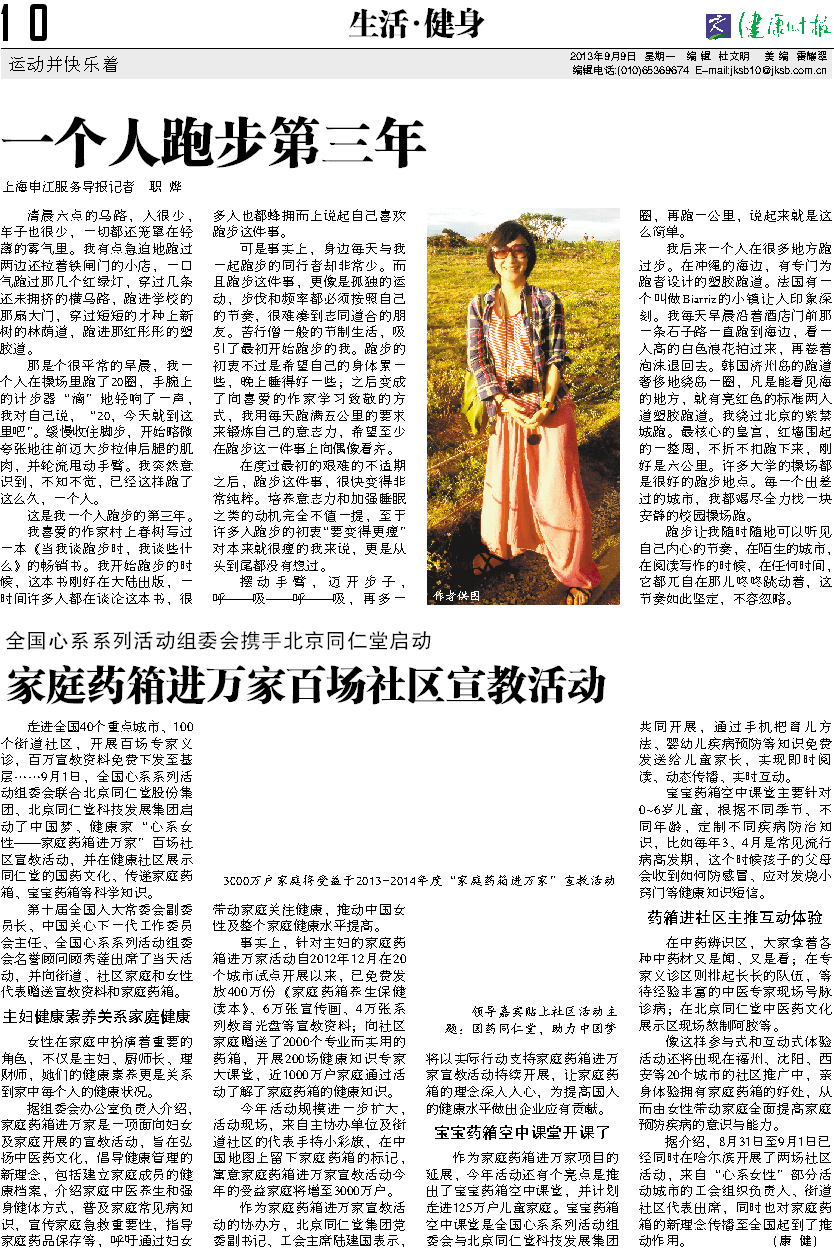

 下一篇
下一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