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6日945期健康时报3版刊发《医生不该说的那些话》引起了读者广泛关注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进行了转发。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在其微博中发表评论表示赞同。
患者最不爱听“不”
在《医生不该说的那些话》中,提出了“六句不该说的话”:1.不知道。2.这事不归我管。3.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。4.晚了,怎么不早来。5.不是做了检查了吗。6.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其中六句话里有五句都有“不”。
患者为何不爱听“不”?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测评中心主任张东分析:“不”有两大杀伤力,第一破坏患者的希望,打击自信心。第二,患者感到被否定,增加患者自我责任。
诸如此类的还有“不能保证”、“你不要抱太大希望”,这些话很简洁,对患者的伤害也很直接。
患者一听到这些话,首先想到的是病不能治疗、不能治愈,其对医院、对医生的信心轰然倒塌,希望向绝望转变。
即便医生的本意也是好的,但往往收到相反的效果。比如“你不能抽烟喝酒”、“你不能老坐着”、“你不能生气”,实际上患者也难理解医生的好心。
这些“不”是对患者生活行为方式、思维模式、心理状态的全盘否定,患者自然而然地产生抵触心理。
如果医生在说“不”前,耐心、仔细地向患者阐明“不”的原因,比如疾病本身的发展规律、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、治疗过程中的意外情况、患者本身的配合程度、疾病治疗的前景等等,患者对疾病有了清晰的认识,其就会保持信心,充满希望。
请给患者多一些信任
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、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,原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赵国秋建议,医生要学会耐心倾听。患者和家属难免有抱怨、愤怒和激动的情绪,医生不要和患者争,应给患者一个说话的机会,让他们一遍遍地倾诉,倾诉可以降低人的愤怒。
其次,学会和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。譬如当患者说“你们错了”、“你们不对”时,可以回答“是,站在你的角度上,我认为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。”有利于平息他的愤怒,等到他的情绪平息后,再来进行沟通。
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庄一强讲了一个故事: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,一个男人骑摩托载着一个女人,前面和后面都有一辆汽车过来,没办法,为了不掉到山下,摩托车一拐弯,摔倒了,后面的女人腿被摔骨折了。
如果两个人是要登记结婚的准夫妻,女人会说:“这么危险的情况下,我男朋友能这样处理,我要感谢他,正是因为他车技好,我们俩才没掉下去。”如果是要去离婚的夫妻,女人会说:“这个男人早就想害我了,幸亏我命大,才没被他甩下去,不然我都没命了。”
一个开头,两种诠释,就是因为两个人的信任度不一样。医生和患者之间也是同样道理,其实总的来说,医生还是为患者着想的,但是患者不信任他,首先在心里为医生定了一个形象:他想谋我的财。医生也会在心里想:得防着点,不然他回头戳我一刀,引起法律纠纷很麻烦。之所以造成这种现状,是社会大背景的原因。医患之间相互不信任从某种程度上讲,是整个社会的局部表现,也是众多不信任中的一种。
医生要专门学“说话”
同样一句话,换一种方式说,就会好很多。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经常遇到患者问:“大夫,有没有一种药或绝招把我的关节炎彻底治好?”温建民说:“如果我说,荒唐,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?患者肯定很反感。我一般轻松地问,您说,如果所有的病都能根治,咱们还不都会长生不老?患者就会明白,自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。”
医学院应届硕士研究生小菲(化名)讲,他八年前听从家长安排,觉得做医生受人尊敬、工作稳定。在大学里,努力学习医学基础知识,中医、西医理论知识都学,而且都争取学得最好。本科5年、研究生3年,没有一门医患沟通课程。他感慨:书本知识都是为了一个个疾病准备的,而不是为得病的人准备的。等到基础课程学习完了,医院实习时,才发现治病并不单单是治疗疾病本身,还要怎么处理与得病的人、与治病的人之间的关系。
相关阅读:
《医生不该说的话》刊发后,许多医生和网友在微博上跟帖,现摘发。
@健康教育何超V: 1989年,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《福冈宣言》指出:“所有医生都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。缺少共鸣(同情)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,是无能的表现。
@张强医生V:语言在沟通中只能传递30%的信息,大部分信息由行为、表情传递。因此,专业性动作和关切的微笑更容易建立医患信任。
@袁钟2010V:“会说话”的确是少纠纷,少扯皮,少冲突,少投诉,少官司的重要方法,而“会说话”需要相当的修养、经验和技巧。
@宋滇文V:不光在医院,很多其他职业场合都会听到类似的回答。一个外国友人告诉我,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耐心、没有修养,面对熟人的时候,他们都是非常友善的。
@梦里轻舟:“会说话”的基础是存在“愿意会说话”的动机,我们的医护人员目前的主要问题尚不是学会说话,而是首先要解决“愿意会说话”的动机问题。现实情况是:相当多的医生更愿意把患者当成一个待修理的设备。“我已尽责”不断成为沟通障碍的借口。当然,这一问题的根源不在医生而在制度。
@不老老兵:文章体现了《健康时报》一贯关注大事的优良传统。这次也很有新意。不是单纯的揭露问题,而是很建设性地、很善意地指出解决医患矛盾的一种很实际的办法。相信多数医务界人士是会认可的,尽管指出的是他们的问题,也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反感。我认为这种方法就很值得发扬光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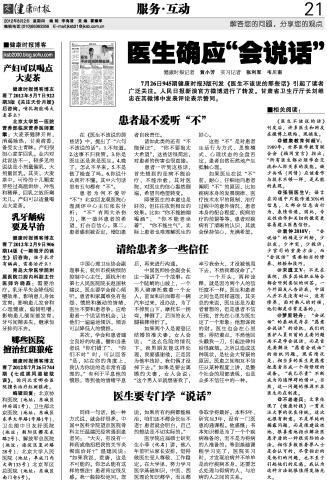

 下一篇
下一篇